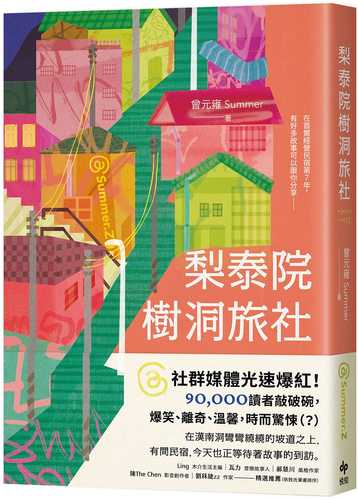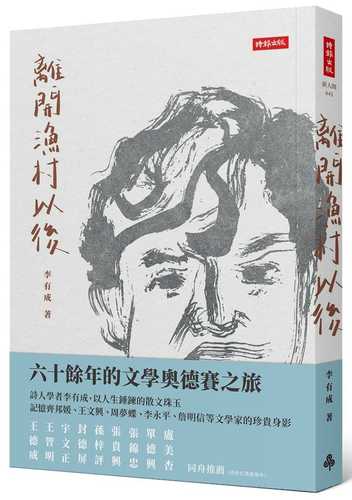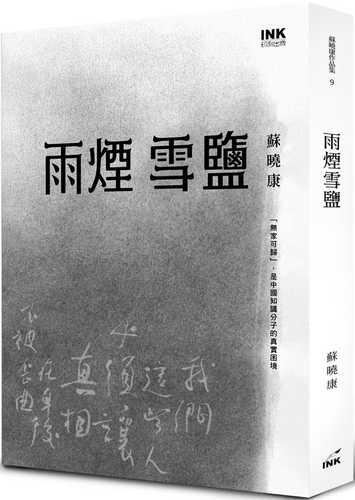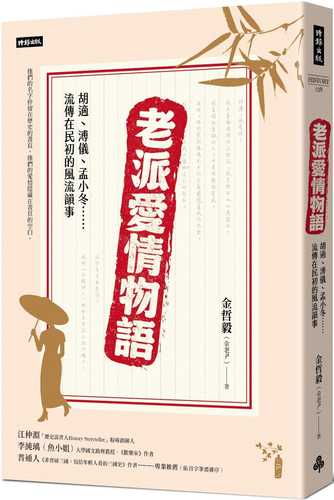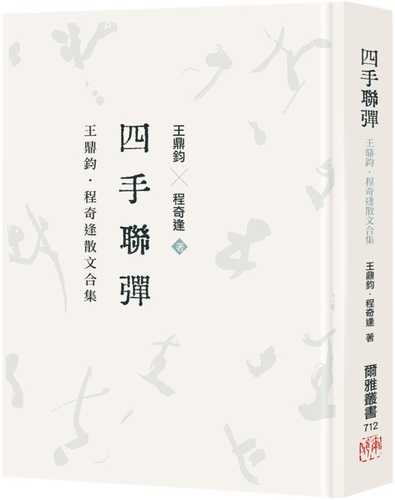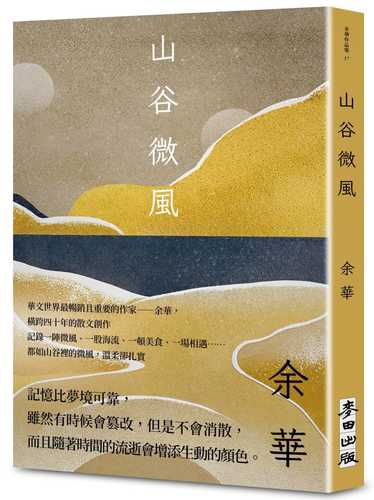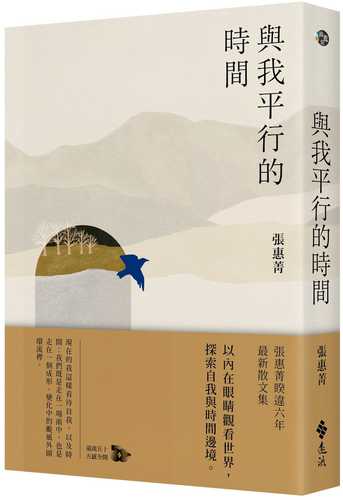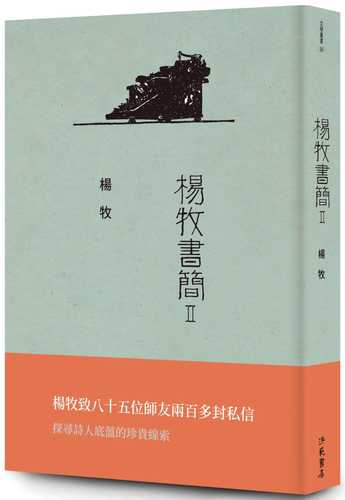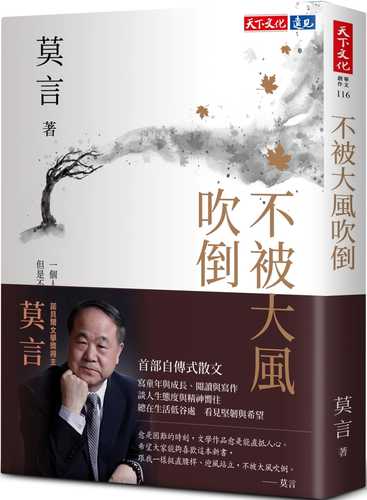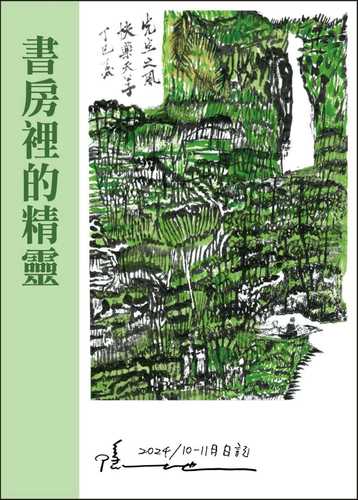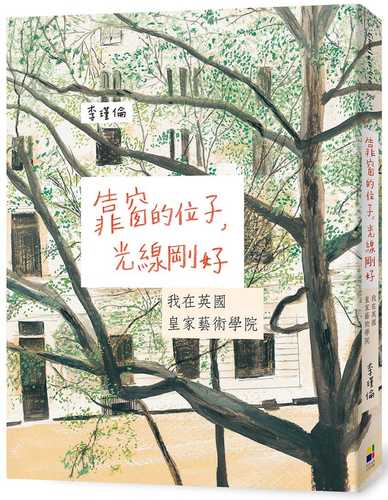老轮船妄图离港,
她刮除覆满周身的藤壶,清装卸重,
却一晌贪欢,陷进洪流,
由此才有旅人的三十三年梦。
落花之梦,以轻为名,却是不能更重了。
宁宁道上人影幢幢,我看到在愁烦心事、在想着自己进行中的小说的三十出头那时以为自己好老人生已走到尽头现在看去多么年轻的自己, 我看到牵着女儿、弯下身子与大头妹说话的唐诺,
我看到二十二岁时穿着长袄打两条及胸辫子、出神出世的天文,
我看到因疾走而长袍角扬起的胡兰成爷爷,
我看到盛年时的父母,我看到宏志宣一俩牵着阿朴的背影,大春美瑶和两岁的张容,丁亚民卢非易杜至伟黄宗应这些少年友人,老焦焦雄屏的比我还爱进玻璃小店,一僧一道也似的吴继文和黄锦树,当时的好友萧维政老萧,当时我喜欢的以军郑颖,正益小郑一家,丽文乃菁马各,最能走最会看的俊颖,侯子……更别说坐在婴儿推车里专注两眼不言不笑的盟盟。
我清楚记得他们的身影,他们的笑语。
我第一次来京都(一九七九)至今,樱花已开过三十三次了。
她刮除覆满周身的藤壶,清装卸重,
却一晌贪欢,陷进洪流,
由此才有旅人的三十三年梦。
落花之梦,以轻为名,却是不能更重了。
宁宁道上人影幢幢,我看到在愁烦心事、在想着自己进行中的小说的三十出头那时以为自己好老人生已走到尽头现在看去多么年轻的自己, 我看到牵着女儿、弯下身子与大头妹说话的唐诺,
我看到二十二岁时穿着长袄打两条及胸辫子、出神出世的天文,
我看到因疾走而长袍角扬起的胡兰成爷爷,
我看到盛年时的父母,我看到宏志宣一俩牵着阿朴的背影,大春美瑶和两岁的张容,丁亚民卢非易杜至伟黄宗应这些少年友人,老焦焦雄屏的比我还爱进玻璃小店,一僧一道也似的吴继文和黄锦树,当时的好友萧维政老萧,当时我喜欢的以军郑颖,正益小郑一家,丽文乃菁马各,最能走最会看的俊颖,侯子……更别说坐在婴儿推车里专注两眼不言不笑的盟盟。
我清楚记得他们的身影,他们的笑语。
我第一次来京都(一九七九)至今,樱花已开过三十三次了。


 放入
放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