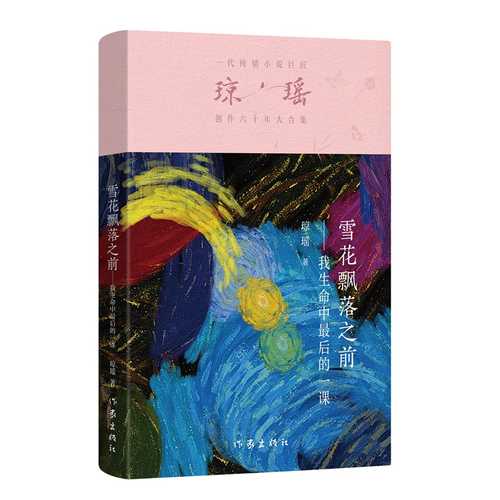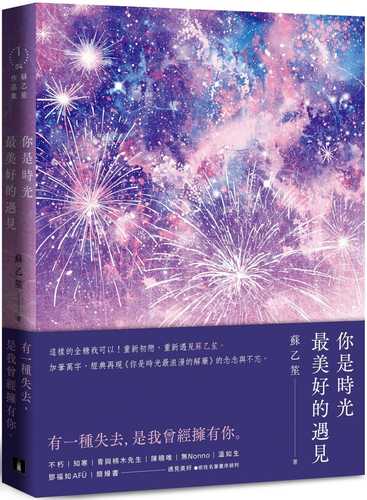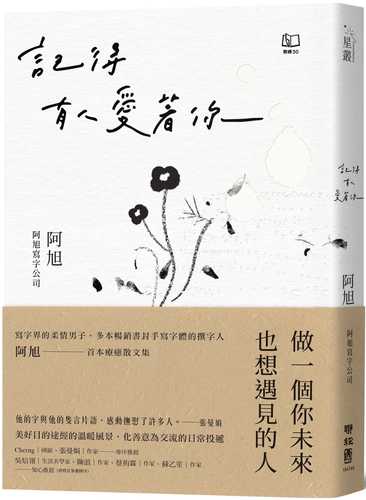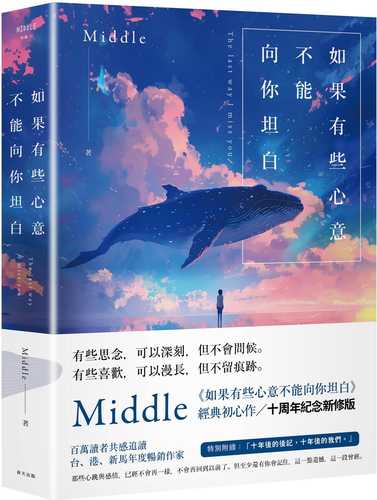女性漸漸確定的事實是:我們自己「不是什麼」,不是被男人界定過的什麼。
這個不是,那個也不是:女性既不等同於男人眼裡的「乳房」,亦不等同於男人心裡的「鄉愁」。但女性到底是什麼?「女性特質」又是什麼?
到目前為止,譬如說,我們尚且不能夠表述,哪裡是我們的家鄉?什麼是屬於我們的鄉愁?
或者,像女性主義者西克蘇說的,女性的鄉愁所在正是我們失去的、一向被剝奪的聲音,而我們蜿蜒的、流動的歸鄉之路恰恰是等待:
「一個女性的聲音從遠方靠近我,如來自故鄉的聲音」──平路
這個不是,那個也不是:女性既不等同於男人眼裡的「乳房」,亦不等同於男人心裡的「鄉愁」。但女性到底是什麼?「女性特質」又是什麼?
到目前為止,譬如說,我們尚且不能夠表述,哪裡是我們的家鄉?什麼是屬於我們的鄉愁?
或者,像女性主義者西克蘇說的,女性的鄉愁所在正是我們失去的、一向被剝奪的聲音,而我們蜿蜒的、流動的歸鄉之路恰恰是等待:
「一個女性的聲音從遠方靠近我,如來自故鄉的聲音」──平路


 放入
放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