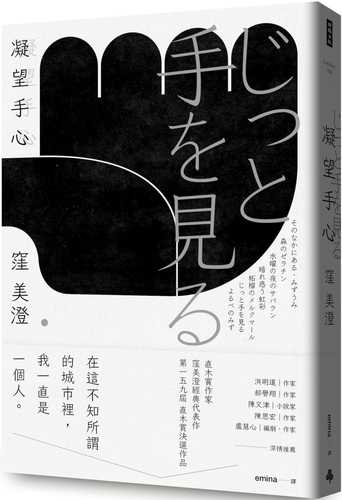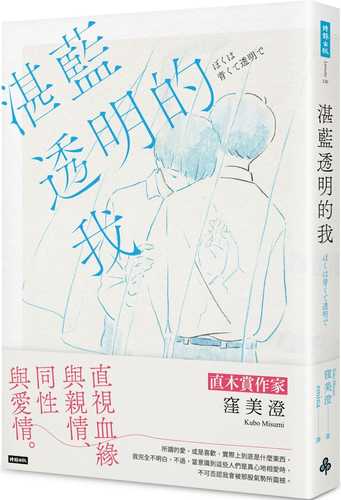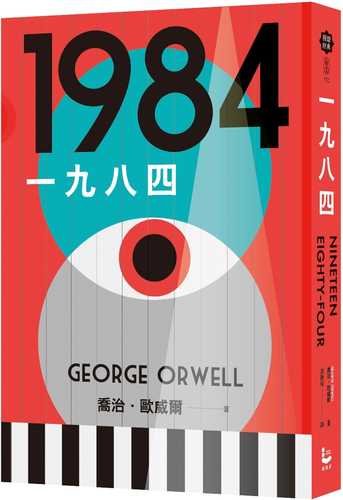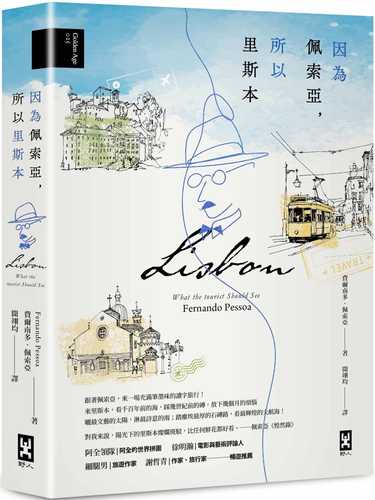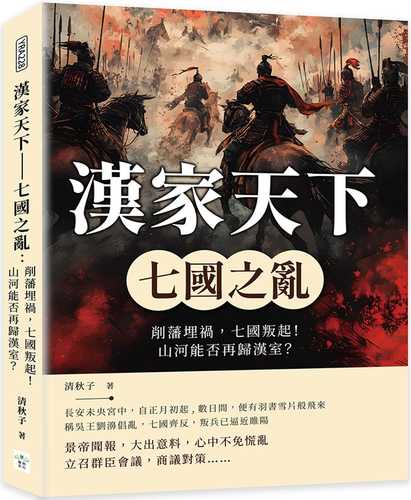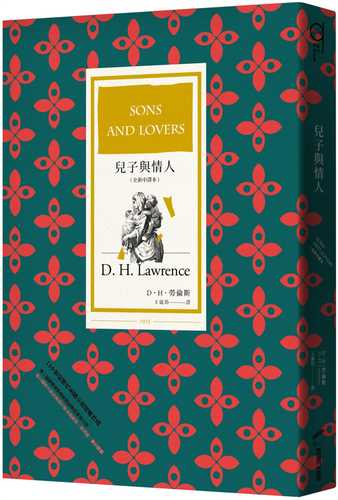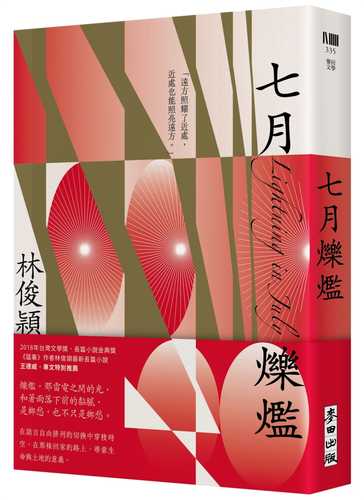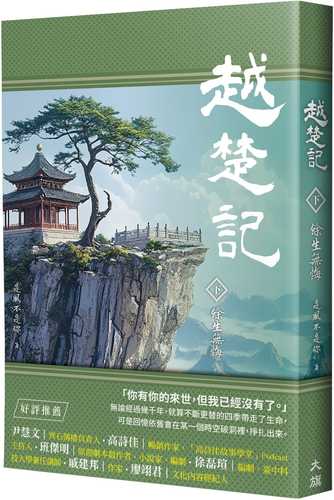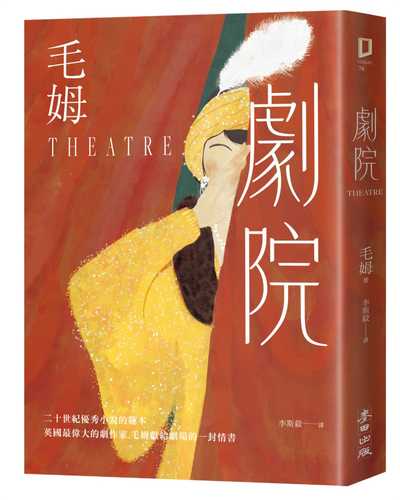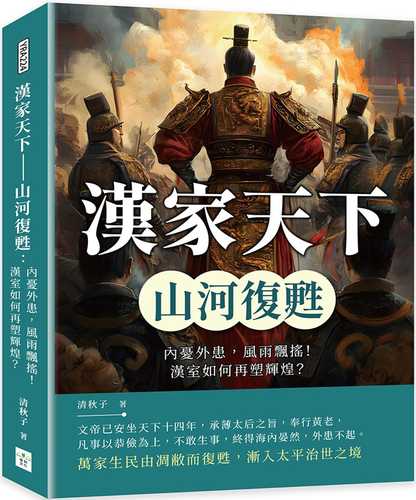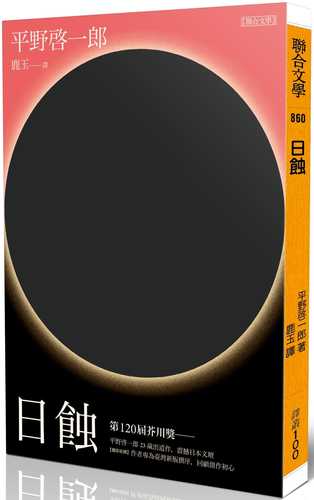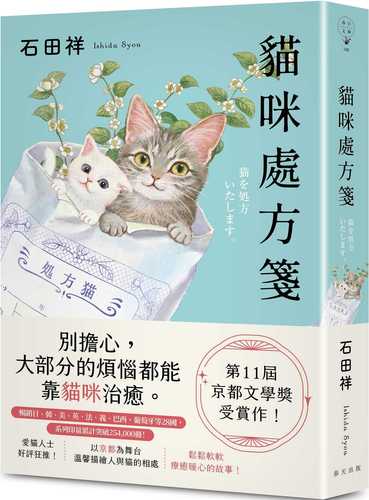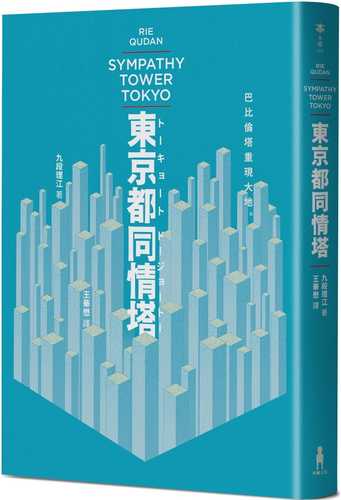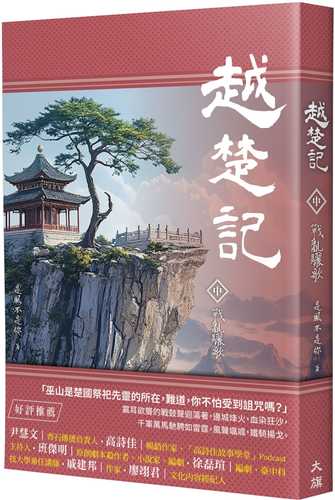既中國又美國的故事……
過去與現在記憶交融……
一九六四年,我高中畢業。高考極其順利,心裡很高興。從來不參加成人舞會的我,就在這個時候,去了一次國際俱樂部,身穿白衫黑裙跳了一支舞。我母親朝著周恩來搖頭擺尾,一臉諂媚。周看看我,問她,「這,就是那個孩子嗎?」她回答說,「就是那個孩子。」臉上陰晴不定,只是卑微地伸出手。周沒有理睬她,卻和顏悅色地問我,「慢四步,好吧?」樂隊就等這句話,於是樂聲響起,我跟著這位交誼舞高手慢慢地踏著步子。這是唯一的一次,我離他這樣近,而且,別人聽不到我們說甚麼。我問了一個問題……
故事是有生命的,如果不能大聲地講出來,故事是會死亡、會消失、會永遠消失的。但是,世間的故事還是在迅速地消失著,因為能夠講故事的人在不斷地走向生命的盡頭。最近三十年,我都在講故事,大聲地講。但是,還是有一些故事,從來未曾碰觸過,因為太黑暗,因為太匪夷所思,因為太過讓人傷痛,或者,實在是太荒謬。二○○三年,我被瘋狂的疼痛折磨已經一年。雖然我們都知道疼痛是生命的孿生姐妹,人還在疼痛中,證明此人還活著。但是,不間歇的疼痛是會讓人感覺消沉的,終於,命運再次展現其威力。二○一一年春夏之交,一個極其偶然的機會,我巧遇一味相當古老的藥物,它抑制了疼痛。我抓緊時機,奮力書寫,講出了這許多近三十年來沒有機會寫下來的故事。現在,我把這些故事交給了出版社。剩下來的事情,便交給了親愛的讀者朋友們。
—韓秀
過去與現在記憶交融……
一九六四年,我高中畢業。高考極其順利,心裡很高興。從來不參加成人舞會的我,就在這個時候,去了一次國際俱樂部,身穿白衫黑裙跳了一支舞。我母親朝著周恩來搖頭擺尾,一臉諂媚。周看看我,問她,「這,就是那個孩子嗎?」她回答說,「就是那個孩子。」臉上陰晴不定,只是卑微地伸出手。周沒有理睬她,卻和顏悅色地問我,「慢四步,好吧?」樂隊就等這句話,於是樂聲響起,我跟著這位交誼舞高手慢慢地踏著步子。這是唯一的一次,我離他這樣近,而且,別人聽不到我們說甚麼。我問了一個問題……
故事是有生命的,如果不能大聲地講出來,故事是會死亡、會消失、會永遠消失的。但是,世間的故事還是在迅速地消失著,因為能夠講故事的人在不斷地走向生命的盡頭。最近三十年,我都在講故事,大聲地講。但是,還是有一些故事,從來未曾碰觸過,因為太黑暗,因為太匪夷所思,因為太過讓人傷痛,或者,實在是太荒謬。二○○三年,我被瘋狂的疼痛折磨已經一年。雖然我們都知道疼痛是生命的孿生姐妹,人還在疼痛中,證明此人還活著。但是,不間歇的疼痛是會讓人感覺消沉的,終於,命運再次展現其威力。二○一一年春夏之交,一個極其偶然的機會,我巧遇一味相當古老的藥物,它抑制了疼痛。我抓緊時機,奮力書寫,講出了這許多近三十年來沒有機會寫下來的故事。現在,我把這些故事交給了出版社。剩下來的事情,便交給了親愛的讀者朋友們。
—韓秀


 放入
放入